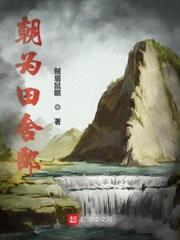笔下文学>折鸾枝 > 第4章(第1页)
第4章(第1页)
>
“所谓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你不想嫁吴家,理应景瑜去帮你。而我若擅自将你藏起,岂不是容易被他误会我与你有私情,做出不和礼教之事?何况,他本就是个多疑的人。若哪一日,他揪住这点不放,我该如何去说?”
他声音清冷,一副拒绝的模样。
这对叔侄关系微妙,她不是不知道。
夏南鸢低下了头,声音,低低地道;
“可若是,我与他没关系了呢?”
“你说什么?”
谢云络愣怔,像是没有听清,许久,他才自嘲一笑:“这又与我有何干系?”
然而夏南鸢抬头,突然正色道:
“七叔,这一路跟来,我知道那个床榻上的人对您很重要,不然,您也不会找一堆尸体作为掩护将他带来吧?我可以帮您救他,只要,您能让我在您的府上躲一躲!”
夏南鸢的声音有些发颤,毕竟,他可是本朝,唯一能跟吴御,甚至是梁王针锋相对的人。
就连她在夏府里的下人们都说,谢世子虽然生性高洁,但在战场上,却如龙腾蛟跃,难掩锋芒,一举将夏国的边境推进了二十里。
若非两年前,他班师回朝的途中,路过青州老家时突染恶疾,至今未愈,西南地方上,也轮不到梁王掌权。
此时,谢云络放下了手里沾了血的锦帕,看都不看她一眼,道:
“就凭你?”
“是,就凭我!”
她跪坐起身,突然正色道。
于是,在他看向她的瞬间,她立马将他丢给她的小药瓶打开,把里面的药全都撒在伤口上。
这药是他给的,总不至于去害她。
当所有的药,全都浸染进伤口时,一股剧烈的疼痛再次袭了过来,她紧咬着牙,直到那些血水,慢慢地流尽,她才感到一种极致的麻木中,带着一股清凉。
这应该是很好的止血药。
但是,还不够!
她将小药瓶,缓慢的收好,之后便用右手去够萧军医旁的一把剪刀。
就在屋里其余的两人疑惑不解的同时,她已经拿起了镊子,夹起一根穿好针的羊肠线。
夏南鸢先是用剪刀剪断了伤口处残余的线,之后单手握线,好的那只右手一边用针穿透皮肉,一边打着结,熟练的,就像是在缝一块衣物。
一时间,屋里的两人全都惊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