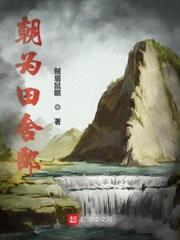笔下文学>我所行之地翻译 > 第143章(第1页)
第143章(第1页)
>
有时候她们就静静地看着他喂食,温声细语地劝他站起来,别把新做的袍子弄脏了,免得浣洗的下人怎么洗也洗不干净。
绯色的宽袖垂在地上,蹭上鸽子争食拥挤掉落的绒羽,还有地上的沙砾。他弯下眉眼,连连应着声,却依旧贪玩,并不舍得站起来。
还有很多事,李融的身体慢慢放松下来,侧躺着沉进这样的暖意里。他渐渐睡沉了,胸口平稳地起伏着,想起很多和薛珩隐约有关的事。
平日的疲累不至于都要带进梦中,房间里的灯熄灭了,窗外的白光顺着窗帘透进来。他听到自己和薛拙之论道的声音,对坐到夜半也不知腹中饥饿,只是由着伙计不断添茶倒水。
又或者对坐饮酒,地上皑皑落雪映着屋中刚添过新炭的暖炉,自己分辨着,眼前的一切都是模糊的,又都是那么清晰。
那是他伸手就能碰到的,争论着,辩解着,到底是谁醉了。
隐约,还能听到一声轻笑,又或许是一两句调笑。
番外三
薛珩不会让他等太久,李融刚开始就对此深信不疑,结果也的确如此。
他并不清楚薛珩和他们完成了什么交易,这几天负责自己的研究员也只是一遍又一遍确认着他的生理健康状况。
想从他们口中再问出来什么话,他们都只是摇着头说不清楚或者干脆搪塞过去。
直到顺应着他们的安排,被推着轮椅走出研究中心的时候,李融才有了更多的实感。洒在身上的阳光带着暖意,风吹过树叶悉窣作响。
银白色的建筑耸立在地面上,严密的结构却意外简洁。他很清楚里面有着最先进的仪器,每时每刻都在测算着他看不明白的东西。
李融只是下意识回头望了一眼,身后也只有穿着白大褂或者防护服的研究员来来往往。
他回忆起了那么一个瞬间,大概是他第一次来到研究中心做身体评估,第一眼看到的,就是这样的画面。
那时还是新春,周围的树还没有抽出新芽,于是光秃秃地伫立在这里,挺拔而孤独。
现在已经枝繁叶茂,宽大的叶边染上了一抹黄色的线,紧紧贴合着。他笑起来,看着薛珩一步步朝他走过来,和推着自己的研究员打了一声招呼。
剩下的那声招呼,是薛珩推着他走过背离研究中心的小路上打的。他现在的声音比李融脑海中的要更低一些,但连第一次见面的那种生疏也没有了。
初秋的风逐起一片泛黄的叶落到他们面前,他们之间还有些沉默。李融觉得,这可以归结为一种无所适从,他好像已经在里面待得太久了,所以身体上的感知变得很迟钝。
现在啊,已经到秋天了。他后知后觉地想起来,他们俩现在待的地方,也该是旧时长安的一部分。
“我之前记过这里的地图,不过现在走出来才发现,这里确实和当年很不一样。”李融听到薛珩开口,他伸手捡起了落在他膝上的那半片残叶。
怎么会一样呢,从小路走出去,周围也都是林立的大厦。街上的人倒是一样多,却都奔波于自己的事情,即使现在是正午,也断没有像长安城里那般日夜不绝的熙攘。
偶尔有人侧目看向他们,李融注意到的话会同样看过去一眼,更多时候是向薛珩介绍地图上写到的建筑。
就算他也很久没有出来走动过,但是向薛珩讲一些曾经熟悉的建筑或者技术还算有余。李融没问薛珩要去哪里,实际上他们都不着急去往一个能停下的地方。
就如同薛珩当日所说,他们都与曾经到过的地方,阔别已久了。
那些曾经熟悉的东西,早已被科技发展的产物取代。李融自己都有说不上来的地方,更何况是薛珩呢。
望不到长安月的宫殿在那场大火里化成了灰,地上散落的沙砾在千年间怕也是换了一遍又一遍,原本是没有人能分得清楚的。
李融落下了话音,自己已经将知道的东西向薛珩说了个遍。似乎终于涉及到了他不了解的领域,薛珩只是静静地听着,没有发出什么声音。
如果没有滚轮的声音,李融甚至觉得,有那么一瞬间,这里就只剩下自己一个人。没有薛珩,没有一个能告诉他真实和虚假的界限的人。
写在纸上的经历不过是实验当中的副产物,要是药剂到最后都没出现什么问题,自己也会忘记那些事情。
只是偶尔夜深梦醒,从无尽的彷徨里听到心脏急速地跳动,错以为自己不在此间,眨眼一瞬后又重新变得恍惚,安慰自己不过是梦。
不过是连他自己都想不起来的梦,但他会永远记住心悸的感觉——就好像自己忘记了好多事情,连带伸出手的时候都不明白指尖为何颤得那样剧烈。
李融收回了视线,突然想要伸出手看看自己的指尖,不料滚轮突然碰到了石子,发出嘎吱的声音。他身后的人却抓得很稳,连带他其实都没有什么特别颠簸的感觉。
他真的记住了吗,他真的忘记了吗,他真的觉得模糊吗——这些事情终归会有确定的答案。李融呼出一口气,思绪仿佛被刚才那一刻的事故打断一样,强迫着自己不去想这些。
他们走了很远的路,自己是这样,薛珩也是这样。李融翕动着嘴唇,总觉得自己该继续说些什么,又不知道自己还能说些什么。
被关在研究中心的时候,他没有机会去看有关后商的史料。现在和薛珩待在一起,他就更没有理由从那短短几行里去看千年前的故事了。
如果愿意的话,他自己一个人就能从那些痛苦和惶然的记忆中拼凑出所有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