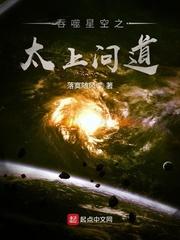笔下文学>我所行之地翻译 > 第137章(第1页)
第137章(第1页)
>
见出了城,沈逸方研墨提笔于车厢内的小桌上写着将要呈给天家的奏章。无论赵家还有多少手段,从江都到金陵,密报上所查到的讯息足够天家定罪了。他下笔有些踟蹰,顿了片刻之后还是如实写着自己所见所闻。
又难免想起章洪,沈知延等人所口述的话,弯了一瞬眉眼之后落笔写完了最后几个字。现在就等墨迹晾干,一路送到长安城中即可。
从长安到江南是日夜赶路,不曾歇息。自金陵回长安,沈逸也打算照样行——他攥紧了袖间的密信塞得更深了一些,只剩下这一封没能寄给薛珩。
罢了,等他到长安再送给薛从之应当不会误了事宜。忙于筑巢的新燕偶尔发出几声鸟啼,离开金陵城后,清风送进来的便不再是时时都有的脂粉气了。
往往是浅淡的花香,飘进来的时候总能慰人心怀。过了这夜后,沈逸才觉出一些疲惫来。他闭上眼靠在轿厢边睡过去。
再有几日,他都算得分明,昼夜不休,他就能快一日接回自己的阿姐,也能快一日见到阿娘。若是有沈婠在身边,霍氏自然能多走动走动,不至于仍旧闭门不出。
不知道等他归时,长安的花会不会早谢。方是日暖,是该给侯府添些白鸽了。他有很多话可以讲给沈婠听,也会有更多空当去陪霍氏。
就当是让他歇一歇,这一遭之后就算功成身退,天家如何,赵家如何,沈骞如何,薛从之如何都与他没有什么干系了。
沈逸慢慢睡过去,将今岁和去岁的纷杂诸事都抛在脑后,他在这样的颠簸里睡得格外安稳。高悬在天边的月正是圆时,无雨无云,送着将要远行的车马。
直到被剧烈的颠簸晃醒,沈逸才从难得的美梦里醒来。起身躲开从侧边刺进车厢中的弯刀,他跨过车夫的尸首,从还温热的血水里扯下缰绳,翻身坐在马背之上。
夜黑风却静,仗着霍岳还教了他些功夫,沈逸从来人手里夺了把弯刀握在手里,才握着缰绳调转马头。
派来的随从相互砍杀的并不在少数,又在夜里,他分不清何人站在自己身边,也不知道何人能得令护下他。
他只能握紧刀柄,借着苍茫月色看清了来人打扮——均是麻衣草鞋,比之刺客,确实更像沈知延所说,赵青近日所忙之事,流民?
流民,他仰头笑出声来,夹紧马腹从人群中冲了出去。来者是谁都没那么重要了,赵家的人,受惠于赵家的人,又或者是自己身边随从上面的主子,都挡了他还家的路。
流民求财谋生,不至于一上来就一言不发,只管举起刀剑砍杀。他看得分明,从那雪白的刃面看到不断喷涌的鲜血,在夜间看到横尸数具,也看得清楚,无论是谁,现在要取的就是自己的命——他沈自行的命。
他策马掠过挡路的人,无论是自己曾经的随从,还是打扮成百姓模样的“流民”,顾不上自己头一次见血,头一次杀人。
颈间的血喷在摇动的马尾上,沈逸勒紧了缰绳,驾着马往远处去。
他已经答应了他的阿娘,马上就要回到长安去了,路上刀兵,眼前血景,都将是身后事。路途迢迢,他都要一步一步走过去,无论其中艰险,无论白骨青泥。
沈逸掩袖擦干溅到面上的血珠,激起几分血气,带着身下的马转圜在来人之间,几刻周旋都没能让他们近身。
只是他终归不像他的外祖,沈逸握着刀柄,想要抵在地上撑身站起来。近处马匹的嘶鸣响得嘹亮,满目都是躺倒的尸体。
耳边却没有其他声音了,沈逸仰头看向仍圆的月,慢慢地,将自己撑起来。他不能停在这里,他不知道自己该往哪里去,但只能走下去。
离开随时会出现的刀剑,离开如今的境地。他将自己撑了起来,慢慢地,往前走着。
他不在乎浑身的疼痛,不去想方才自己取了多少人的性命,只是有些可惜车厢内写好的奏章和密信——怕是送不到长安去了。
沈逸没去管身上的刀伤,衣袍被涌出来的血打湿,他只是往前走着,踏上这条归家的路,他好像离长安很近很近,又分明离他的家很远很远。
但他总要回去的,讲给他的阿娘和阿姐听,江南的花开得好看,侯府也可以在庭院里多种一些。
他笑起来,从眉眼中可以窥得霍氏的几分容颜,便也笑得跟霍氏一般好看。
沈逸走着,微风吹过他沾血的外袍,原本金色的绣线和其上的祥纹都被一层又一层血盖住了。直到听不到其他声响,才觉出几分疲累来,握着刀坐下来。天色依旧黑沉着,还没有到该天亮的时候。
沈逸用手撑着地,想要去摸身上依旧淌血的伤口时,才发觉出自己坐在了小河旁。如今身边没有油灯,没有烛火,他只能听到耳边隐约的嗡鸣声,大概是草中的蚊虫吧。
他捧起双手洗干净了脸上的血迹,想要撑身再站起来,归家的路就在眼前,沈逸沈自行,不能不行此路。
可他又忽然被躯体的沉重绊住了,即使手指攥得再紧,插进土里的刀刃再深,他都无法再站起来了。
沈逸挣扎着,咬死自己的下唇,尝到一股又一股血腥气。终于踉跄着站起来,又突然倒下去,倒在河水里。
手指从刀柄上滑落,衣袍上的血被河水晕开,在碧绿的水边开出一簇又一簇胜花的红来,像是通明的油灯,又像是冬天燃起的炭火,最像被北风吹散的烛火,烧起满江春色。
却丝毫没有那股灼烧感,江南的冬是暖的,江南的春只会更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