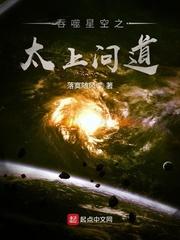笔下文学>我所行之地翻译 > 第48章(第1页)
第48章(第1页)
>
再细看过去的时候,混着岸边泥沙的水面又同往常一样平静着,四下无人的时候更显出秋日的寂寥,纵使北风呼啸而过,也只是平静着,或者说死寂着,任其上的浮木漂流而下。
李融向外看的时候,通常只能看到薛珩骑马远去的身影,走在前面仿佛给他们领路一般。只有偶尔在茶棚歇脚的时候才会坐下来饮茶或是喂马,租来的马也疲倦着,不断嚼进马厩中的干草,时而发出嗡鸣的鼻音。
他忽然想起那日论道的光景来,薛珩,薛拙之,当真是上好的字。相逢结友同行,他仍觉得薛珩身上有很多他看不透的地方,那些没有办法深问的事情只能同未解的道一样藏在他的心里,却依然欣赏那份抹不去的悠然。马蹄踏在泥泞的地上,薛珩也走得极快。偶尔瞥见人和马俱远去的身影,李融总觉得下一刻他就要消失在自己眼前,像只南迁的雁,不知道将会落到哪片深林中去。
他收回目光去看近处的景,马车在后面走得依旧很慢。入了中原天空便开始飘下淅沥的细雨,扬扬洒洒落地无声。被风吹弯的草泛上枯黄,又被车轮碾在泥泞里再看不真切。李融撑着未眠的疲惫咽下将要发出的叹息,按照时日算,他们应该快到河内郡了。
薛珩有意放慢了脚步,跟在马车旁走着。马也在连日的疲倦里消瘦下来,深秋的风吹得更冷一些,李融和苏肆都裹上了在临沂采买的新衣取暖。中原在今朝分治成数城,有些便如颍川一般,始终屹立在平坦无垠的原野上。有些就如河内河东等新划起的地界,城墙往往只建了一半。他们坐着车匆匆而过的时候,便不像在江南一般困于人群拥搡。苏肆跟车夫结了剩下的账,李融则自己下车来。
薛珩早就下了马,将马也一并交付车夫带回去。李融见他摸过那匹马的鬃毛,马温顺着低下头去,和这几日一同相伴的饲主亲昵告别。
“拙之。”他开口唤了薛珩的字,抬眼就能看到薛珩未收的几分意气来,才想起薛珩比自己还要小上一岁。骑在马上除了悠然也能显出少年人的豪情,只见薛珩同样抬手作揖应下自己的话,“今日便到河内了,子衢可有什么安排?”再抬头的时候,薛珩便同往常没有分别,面上挂着淡笑来,和他亲近着,又好似没有那么亲近。
李融敛起分散的心神,顺着薛珩的话思考过行踪。几日连续的赶路让他疲倦着,久卧在车厢里蜷曲着身子。如今下车被秋日的凉风吹过,才有几分清醒。进出河内的人群比临沂城内的百姓要多,就算比之姑苏金陵等地也不差分毫。
“两位公子不如先找客栈边歇息边说?”苏肆背过行囊插进去话,薛珩道声好,李融也顺着两人意思歇下心神往附近的客栈走去。河内郡里往来的人虽多,也没有江南那般人声鼎沸,甚至不如临沂吵嚷。
李融和薛珩落在后面,由着苏肆带路。李融走得格外慢些,细瞧着周围的人。深秋时节本是丰收已过,郡内的人却少见喜色,平淡质朴的面容千篇一律,只是低下头匆匆忙忙来往着。叫嚷揽客的商贩也分得清人,通常只看穿着打扮像外来客的招揽吆喝。还有剩下吵嚷的,便是角落中行乞的人,衣衫褴褛地缩在一旁,或躺或跪在尘土里目光一遍遍勾勒过来来往往的人。
他解了钱袋往缺角的碗中落下几枚铜钱,亦知不可露财的道理。薛珩走在他的前面,似乎也同他一样看过身边来往的人,又似乎只是看向再远处的地方。李融又加快了脚步,跟紧他们,在客栈歇下。住店的人不多,伙计很快就收拾好了厢房领着他们上楼去。
薛珩自己付了银两,单独住在临街的那侧。李融这次选好的厢房靠西,窗也开在远街的那边,听不到什么声音。小二很快上了沐浴的热水,李融解下发带跨进木桶中,湿发贴在背上,发尾则浸在水里散着。
他慢慢梳洗着,濯净近日沾染的满身风尘。热水熨烫过酸软的腰腹,李融披上干净的外袍用棉布吸着发尾不断下滴的水。屋内的漏钟同样滴下水滴,还未及日落时分,窗外却安静着。他躺上床榻睡过去,准备缓和连日的疲累。
鸡鸣一响,李融便清醒过来披衣下床开了窗。天色还未完全亮起来,日月同待在天边相互辉映。远街的巷子里也堵满人了,地上的霜被踩踏得干净,秋风卷着枯叶往下落。大多都穿着破烂的长衫,小童被父母抱在怀中啼哭着,均是蓬头垢面等着有城中的人醒来,准备去先讨碗水喝。没醒来的占了少数,横陈在地上的大多是病了或是残了的人。
他虽离得不远,但是再难看真切了。只是沉默地用着朴素的饭食,喝着温热的稀粥倒不觉简陋了。河内离颍川算不上远,所以自己方才见到的人大抵都是从颍川各县逃难而来。本该是秋忙的时候,他也曾在竹卷中读得中原的繁盛。如今只见得卷中数不清的人拥挤在一处,自己也只能感叹天灾如此。
由着小二收拾掉碗碟,他对镜正过衣冠敲响了薛珩的门。“请进。”李融推开门走近,薛珩也刚用完饭菜,坐在桌前研墨准备写画些什么,“原是子衢来了。”
薛珩停了动作邀着李融坐下,接了清水放在碟中让半干的笔毫晕开。“怕是多有叨扰,拙之准备作何文章?”李融帮他铺开绢布压好发问。
“途中见秋日光景,乘兴而作,还未落笔,子衢前来便不算打扰,”薛珩答过这问,看向李融仍带疲倦的面容,“子衢忧心何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