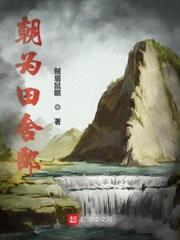笔下文学>我所行之地翻译 > 第16章(第1页)
第16章(第1页)
>
树枝插进未干的沙土里,他们避过不时从山顶滑落的碎石块。今日的云散了大半,太阳能够照着地上了。身上的麻衣也干透了,不过还是带着冬日的冰寒,伤口的疼痛也被这样的温度麻痹着。支撑他们往前走的,只有眼前的村落。
李河再次咬破下唇,之前没有好的伤口带来细微的麻痒,他和蒋二需要再走过半山腰这段荒草丛生的小路,就能一直顺利地往山脚走去了。他们分外小心着,拐杖一次比一次落得更小心,以迟缓的速度拨开挡路的荒草,往下去。
山脚的地方总是会有人过来的,于是山路也被走宽变得平坦一些了。蒋二用剩下的力气开口了,这两日的沉默几乎要憋坏了他,他笑出了声来,发自内心的喜悦,“小兄弟可是要到家了啊。”李河也顺着他的话点点头,“可以好好歇脚一阵了。”他们互相搀扶着,从山脚慢慢走下去,当然,带了马上要到达的急切。他们用上了自己最后的力气,很快便走到了村口。
村里是难得的死寂,李河先瞥了一眼村口的井,井口还有没被放下去打水的木桶。他浑身凉透了,缺了肉的死人就倒在井口,他松开手腕丢掉了一直倚靠的拐杖。他没有力气去想了,他这样想着,跪坐在村口,蒋二也同样蹲下来,缓着刚才看到的一幕。
黑色的鸦大摇大摆饱食着这些腐肉,地上的血块凝结了,混着冬日的霜和沙土连在一起。李河觉得自己的胸口堵了一口气,或许那是一块淤血,他几乎愣怔地保持跪坐的姿势。腰间配的弯刀在地上敲出浅浅的沟。
是谁来到了这里,为什么有这么多死人,为什么没有人来处理?思绪并不会因为他的强迫而停止,那一定是一伙胡人,一伙他们没有遇到的胡人,或许就在他们离开村子的第二天,白天才会有人去井边打水。他们闯进了村子,抢走了各家各户的粮食,并且杀光了这里的人。
不会有第二种答案了,李河伏下身子,将头重重磕在地上。额角出了新鲜的血,几日赶路的疲累,肩上疼痛不已的伤,和到达村口的喜悦全都凉透了。他觉得自己身上正在流动的已经不是自己的血肉了,而是冬天结冰的河,任北风穿堂过,空透地看着这一切,却不能无动于衷。
血块好像哽到了他的嗓子里,他起不来了。眼眶憋着久没有落下的泪。蒋二用刀赶走啄食尸体的老鸹,粗哑的鸟叫此起彼伏地响了起来,响彻这个完全死寂的村子。眼里的水还是没有落下,他抬起头,眼睛平静地看着天上的太阳。李河开始觉得,自己的身子开始僵硬,从骨子里开始僵硬,他好像正在被鸟兽吃着露在外面的血肉,白骨也开始被太阳照到了。
这是大白天,冬日难得有暖阳的白天。他就这样跪在村口,肩上崩裂的伤口继续滴着没有凝结的血液,一滴一滴,沉默的血色滴在了那小一滩沙土上。很快被风吹干,像极了贵人的胭脂,而陇西惯常是见不到这样的胭脂的。
第十一章
李河察觉不到肩上的伤,也察觉不到开在地上的血,只有风吹透了他,而他已经没有力气站起来了。蒋二也融入到这样的沉默里,等着李河缓过来。他依旧跪在那里,仰起来的头又重新低下去,他没有来打过几次井水,也不认得井边死着的人。他只是……只是什么,他只能强迫自己不再想下去,呼出一口浊气,留下一声长长的叹息。
哽在喉咙里的血块好像还没有消失,他拣回松开的树枝,哽着沙哑的嗓子发不出来声音,他想对蒋二说,跟着他。李河回头看了一眼蒋二,几次张开的口都没能发出他预料的声音。于是他知趣地恢复了往常一般的沉默,即使这沉默跟往常也相差甚远。他在村道里走着,这里再也不会有零散的炊烟升起,也不会有黎明时分的鸡鸣。
他觉得自己的记忆有些模糊了,他离开了多久呢,分明他好像昨日才从这里离开,又好像已经过去了很多年很多年。躺在村道和屋门口的尸体比比皆是,偶尔有一两具是胡人的。他们手上的弯刀沾了厚厚的一层血,他们倒是闭上了眼睛。但大部分村里的人,眼睛还睁开着,直直看向天,直到被鸟雀啄空脸上的肉。
李河就这样走着,也不管蒋二有没有跟上了。他迈出一步又一步,寒风吹进他的血肉里,太阳的温度在此刻变得越来越冷,照下来的光刺痛着他的眼睛,风干眼角未落的泪。他忽然又走得极快,不知道从何而来的力气,去按照记忆里的路,找到老伯的家里。
他找到老伯了,就躺在草帘下面,从胸口涌出来的血一直流到屋檐外的地方。草帘被风吹得七零八落,幺儿呢,就那样躺在床上,身上的草席被血染红,又变成如今的黑色。李河就这样愣怔地看着他才辞别没有几日的故人,他们应当算得上是自己的故人。
他还能记得,这样的清晨,历来是老伯先在鸡鸣声中醒来,拖着不便的腿脚开始剧烈的咳嗽。然后去生火熬菜汤,幺儿会多睡一会儿,直到热气飘进屋子里才会吵吵闹闹地下地。鸟雀还没有飞到这里,冬日的寒风吹尽了血留下的腥味儿。
李河想,他们就这样保持着生前的样子,好像并没有死去。他又握紧了拳,闭上眼去想他们的确是死了。老伯不会再拖着腿脚在傍晚的时候和幺儿一起去井边打水,也不会再在这样的清晨背着背篓去城里的铺子卖晒干的草药。幺儿不会再在清晨起来进山去替老伯摘草药,也不会在老伯咳嗽的时候轻轻替他拍着背。他们再也不用担心来年的粮税了,也不用再担心岁末大寒的温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