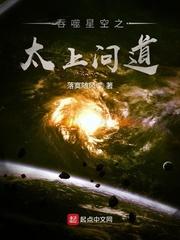笔下文学>我秦始皇被千年后直播了! > 第一百一十八章 战神李牧(第3页)
第一百一十八章 战神李牧(第3页)
寒潮席卷。
豆灯的光亮下,李牧盘坐在蒲团上,一点一点地擦着弯刀,和秦军对峙一年多以来,未曾煨过血。
可擦完之后。
银烁的光亮比外头的寒雪还要刺眼,爽朗地笑道:“撑犁!宝刀未老,犹似当年哈哈哈哈。”
撑梨。
是匈奴语中,天的意思。
大破杀匈奴十余万骑。灭襜褴,破东胡,降林胡,单于奔走。其后,匈奴不敢近赵边城。
他,就是匈奴的天!
是他们日日夜夜的梦魇,更是撕咬他们的恶狼!
“畅快。哈哈哈哈。”
他仰头后靠,回想起那段大草原纵横驰骋,高歌牧羊,篝火饮酒的日子,缩居在这一小小的井陉山里,已然显得无比的憋屈。
至于为什么要领命抗秦?
赵国庙堂上如何的乌烟瘴气,阴暗如一摊臭水,甚至天下名将都被恶意中伤,背上一身莫须有的恶名。
他李牧难道不知道吗?
多算多胜,少算少胜,如今现在,罢了罢了,不算也罢了。
走不出死路,总归是要换一条活路的。
这几十万赵军,苦守井陉一年余,后方的粮草被赵国庙堂拖断,不能眼睁睁地看着被耗死,他们是赵国的兵,宁可战死也不能饿死。
罢了罢了。
老夫能做的也就莫过如此了。
外头声声刁斗于冷夜中响起,风雪已经停歇,寂静的让人心颤。正要掀开帐篷,突觉右臂阵阵刺骨,李牧死死箍住经脉,让疼痛止息。
身后似乎有人在唤他。
他回首。
司马尚单手持缰,苍颜白发转头而视,大吼道:“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自古以来,皆是如此,虎狼敢来,我们只管拔牙卸爪剥他娘的皮!别的一律不理,老夫先去矣,兄弟!你要记住,死守井陉,让那虎狼也尝尝我们赵人的刁勇,做梦都忘不了我们赵人滋味!”
井陉的山木褪色,消磨,枯黄,被覆盖至皑皑白雪,这位和李牧在战场上默契的如刎颈之交的将领一去无踪迹。
再也没有回来。
这段日子像是一把弯刀,不停地刮他,挑开他经脉,放干他血水。
只剩一副骷髅架子,戴上头盔,穿上全副武装的甲胄,披上大红披风。
踩上金靴踏了出去。
在千千万万赵人眼中。
走出来,去成为他们的信仰,成为他们战无不克的战神。
每次接战,李信决然地扛起千斤重担,口齿肺腑一句又一句的:“末将领命!”
命?
什么命。
可他连自己,甚至连同胞,赵国的命运都悲哀地看到头了,自己这只天残胳膊,举起弯刀,北部抗击得了如狼胡人,南部阻挡得了如虎秦人,可他终究抵抗不了历史的车轮。
名唤命运。
的敌人。
死死攥住帐篷的手颤抖不停,李牧仰起头来,一遍一遍为自己,为何还要死守,为何要领命,更为何要背上谋反的骂名。
战场上屡屡和死神摩肩接踵。
真的将荣誉,地位,功勋,官职看的如此重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