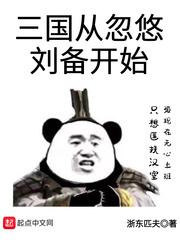笔下文学>和敌国元帅联姻后我离不掉了 > 第96章(第1页)
第96章(第1页)
>
江逸之去而复返,身后跟了准备充足的大夫。
谢砚察觉到他来了,没有回头死死的盯着窗外,如今也算是风水轮流转,想他竟然也沦落到这个地步。
江逸之吩咐大夫帮其治疗伤势,劝诫的话甚至还没来得及说出口,反观他很配合。也对,他们都不是拿不起放不下的人。
半盏茶后。
“公子,那一剑并未伤到要害,伤口较浅,按照方子服药好好休养一段时间,便可痊愈。”
“去抓药吧。”江逸之看着谢砚的眼神始终带着打量,犹豫了半晌他终究是停下了脚步说:“今日之事,姜次他……”
“你不必替他辩解,这是我与他之间的事情,就不劳江公子操心了。”
江逸之这也算是吃闭门羹,直觉中隐隐约约感觉到他对他有种莫名的敌意。
明明两个人已经沦落到这个地步,那曾经的话语有几分是真,又有几分是假,都已经无从考据了。听到江逸之的声音,他下意识地否定,脑海中不约而同地出现沈姜次的脸。他想他大概是疯了吧。入到囧途,还对沈姜次抱有些许相信。
江逸之看他这般柴米不进的样子,木讷之余甚至觉得有些熟悉,就好像曾经的自己。他长叹一口气,事情既然已经发展到这个地步,那么他所能做的一切显得那么苍白无力,他出了牢门,听着链子铁锁狠狠落下的声音,那颗悬着的心始终不曾放下。他回头看了看,随机吩咐道:“派人定期送汤药、炭火、膳食,衣衫,务必照顾好他。”
“是。”
听着渐渐走远的脚步声,谢砚的身体终究是撑不住了,他倚靠着冰冷的墙壁渐渐放心懈怠,手指抚上伤口的位置,还未怎么触碰。他明显地感觉到鲜血涌出,疼痛感包裹着他的全身,每一步都显得很麻木。脑中不自觉地浮现出当时在大殿上的一切,他的一剑、他的决绝,还有他故意……故意让那一剑刺入胸膛,不管今日的事情到底走向是如何的,那种情况下他只能兵行险着,用自己的命的去赌他心中那点子不忍,从而创造生的希望。
他喃喃道:“沈姜次,我也算是利用了你一次,就赌这一次,输了……”
输了,那就不赌了……
不安与失意往往是结伴而行,往往不是一处而已。
“滚、都滚!!无用的东西。”平日最是规矩的褚临在此时却是大发雷霆,在赶走了一波又一波大夫之后,他依旧是不肯相信这个所谓的事实。
整个永安王府的气氛早已经压过了大雪初停后挂在天边的乌云,在压抑、沉重中始终占据着榜首屁。侍从们小心翼翼,甚至是有更甚者那些被压制的野心开始悄无声息的增长。
“你们还不快点去找大夫,京城的大夫不行,那就去请太医,实在不行出京城,天下之大,我就不信没有一个大夫能医得了。”
侍从暗卫大气都不敢喘,因为此时他们的心底已经有了答案。
褚临又何尝不清楚,被太医、京城大夫断言的话,就像是给这件事画上了一个结果、可是……可是,对于他们这些从人群中杀出来,努力博得一线生机的他们来说,拿起剑,哪怕到了最后一刻,那也是给自己留下了一丝生的希望。一个拿不起剑的人在夜北,就像是被折断翅膀的鸟雀,失去争抢的底气,最终只会沦为蚕食殆尽的物件。
他可是沈姜次,那个年少拿起剑,在众多人中脱颖而出的沈姜次,有了剑,有了武器,他才有底气。他褚临无能在这世道护不住他,若是连拿剑的手都保不住……当沈姜次醒来,他又该怎么回答。
就连他也不清楚这到底是第几位大夫了,大夫推门而出的那一刻,褚临立刻迎了上去。还是一样答案。“公子他、手筋被……挑断,当时应该伤得并不严重,可是公子他后来又拿起剑,加上几乎在雪地冻了一夜,旧伤加上新伤,能保住性命已经是不幸中的万幸了。至于公子所求,老朽也是无能为力,还请另请高明。”
希望一次次覆灭,褚临的脚步往后踉跄了几步,他几乎是强撑着身体,“大夫,你再看看,你再看看,说不定是有希望的。大夫……”
大夫难为情地扯开他的手腕,行医多年他见遍了这种情况,救不了他是他身为医者的无能。“老朽,尽力了……另请高明、另请高明!!”
望着他离开的身影,藏匿在心中无声的怒气再也忍不住,褚临一遍遍捶打着柱子,心里不断埋怨着自己,他当时为什么要听他的话,如果他态度强硬一点,如果他能提前一步察觉到其中的异常,如果他……鲜血从关节处、手背涌出,伤痕累累。他望着鲜血横流的手背,躁动不安的情绪一下子被安抚。他回头望着侍从:“还不快去找大夫、去!!”
“是。”
看到他们渐渐走远的身影,褚临几乎是瘫坐在地上。尚未化去的雪曾沾染在他的衣角之下,寒冷他不觉得,手背垂向地面,鲜血夹着这冰雪在寒冷之上开出一片片血腥的花朵。
想他褚临的一生,能珍惜留下来的人和事不多,沈姜次几乎是占据了他生活中的全部。
主子,褚临会用尽一生,去守护你,让你有在这京城中生存的底气。
褚临无用,最后一道防线,我愿意拿我的命去换。
泪水从他的眼角滑落,不慎滴落在雪层之上,那是一个少年最后倔强。
院墙之外,耳边,不断传来动静,褚临几乎是狼狈地爬起来,慌张地擦拭着眼角的尚未干透的泪珠。如今主子病着,他就要替他扛起这里的一切,用尽生命去守护你的底气。一抹鲜血从他的眼底掠过,鼻尖的血腥味仍不曾散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