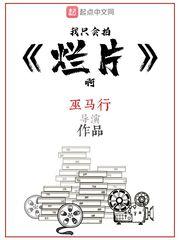笔下文学>帝姬不远嫁七度网 > 第168章(第1页)
第168章(第1页)
>
看起来是在恐吓纯懿,可其实听着的人各个满头大汗,顿时明白自家郎主是来真的,也不敢藏私,只当做纯懿不存在,将大事难事一件一件汇报给延陵宗隐,然后等着他示下。
一个时辰很快就过去。延陵宗隐身体素质极好,处理再多事项,也一点儿不觉得累,可纯懿在旁边看着,他的臣属们早就忍不住换了好几个姿势,有几位年纪大的,甚至在延陵宗隐低头看奏册时,就偷偷去敲后腰,一次都不落下。
纯懿再看看满脸严肃的延陵宗隐,就有些无奈。终于,在他处理完一件事项,马上又要喊下一个人时,纯懿抢先开口:“这么长时间了,我看不然休息一会儿?”
延陵宗隐明显一怔。这又没干些什么,怎么就需要休息了?
可再看看身形瘦弱的纯懿,延陵宗隐猛然醒悟,一边暗恼自己考虑不周,干脆利落道:“既然如此,那就休息一刻。”
二太子的庭议,什么时候有过休息?众人开始还有些不敢动,可看延陵宗隐眼睛已经瞪了出来,恶狠狠看着他们,颇有一副他们不出去他就亲自动手把他们踹出去的意思,急忙纷纷告退,压抑着内心喜悦退了出去。
屋里只剩下纯懿和延陵宗隐两人。纯懿从椅子上跳下来,在延陵宗隐的注视下,缓缓走到他身侧,拎起旁边的茶壶,却发现里面的茶水早已凉透,便干脆将旧茶都倒掉,亲自动手,开始煮新茶。
一边煮,一边有一搭没一搭的与延陵宗隐说话:“听你们刚刚提到七皇子?”
延陵宗隐看她弯着腰,是一个不太舒服的姿势,边将纯懿拉到身边,让她坐在自己腿上,轻易制住她的挣扎,漫不经心地卷着她的头发:“嗯,怎么了?”
纯懿挣扎了一会儿无果,便也随他去了:“我在太子府里时,七皇子待我很好。”
延陵宗隐颔首:“我知道。”
对上纯懿有些诧异的视线,延陵宗隐直接道:“他认为是我杀了他的太子哥哥,来寻我打过架。”
“哦,”纯懿低头,继续去搅拌茶花,轻笑着开口,“那他输的惨吗?”
延陵宗隐一怔后大笑。他将纯懿揽入怀里,在她颊侧重重亲了一口:“有点。若不是知道他照顾过你,我留了手,他输的还会更惨一点。所以他向父王请旨,去蒙古边界带病去了,说要去磨练武艺,回来再找我寻仇。”
纯懿白他一眼,半是玩笑半是真心的:“那我祝他成功。”
惹来延陵宗隐又一阵大笑。
自这日后,纯懿也被迫繁忙了起来,她也要每日早起,跟着延陵宗隐去见他的那些臣僚。去得多了,她对延陵宗隐的书房就熟悉起来,行动间也越来越自如,到了后来,她甚至会在延陵宗隐议事到一半时自行出门去透气,然后带着一捧在前院摘的鲜花回去,不顾延陵宗隐铁青的脸色,将花儿们按着颜色样子搭配成一束一束的,插进延陵宗隐书房那些造型古朴的瓶瓶罐罐里。
延陵宗隐其实不太在乎这些东西,可却很想惹她生气,便故意板着一张脸,做出一副生气的样子:“你知道这瓶子多少钱?这可是几百年前的东西了。”
纯懿已经看穿了延陵宗隐的纸老虎本质,淡定点头,把最后一支花插进去:“哦,怪不得,配这腊梅这么好看。”
延陵宗隐瞪她,可打又不舍得打,骂也不值得骂,最后还是将她抓了过来,从她身上狠狠得了些好处才罢休。
这么一日日的下来,延陵宗隐书房里的花越来越多,他倒是也适应得很好,每次控制不住想发火的时候,看看这些开得绚烂的花儿,再看看坐在旁边人比花娇的美人,延陵宗隐沸腾的怒火总能奇异地消减一些。
算了。
他颇有些自欺欺人地安慰自己:眼看着她就如同这些鲜花一样一日一日鲜活起来,不再是如同一潭死水那般沉闷压抑,也算是有些回报。
延陵宗隐习惯性地侧头看向纯懿,果然,她也正在定定盯着他。两人目光对视,纯懿毫不闪躲,对着他露出一个温柔的笑容来。
延陵宗隐恍然未见般,冷着脸转回头,唇角却悄悄勾了起来,许久都压不下去。
纯懿一直盯着延陵宗隐的动作,就是在他转回头后也没有移开视线。见他提起一方私印,在公文上落下印记,纯懿心中暗暗道:左手第二格抽屉。
心中话音未落,果然,延陵宗隐探手拉开左手旁的第二个抽屉,将那方小印放了进去,然后合上抽屉,用钥匙锁住了门。
纯懿又在心中揣测道:腰间右侧的铜筒。
延陵宗隐将那把钥匙随手丢进了挂在右边的一个青铜简筒里。
纯懿唇边便也勾起一个笑容来。这么长时间以来,她一直在小心观察着延陵宗隐的一举一动,到了现在,也算摸清了一些他的习惯。再猜延陵宗隐的行动,倒是十次有六七次能猜准了。
纯懿很受鼓舞,看延陵宗隐暂时没什么动作可以让她观察了,便重新去听那些臣属说话。
那个叫木沐的正皱着眉头汇报:“……属下已经命人去查了,的确是蒙古国王子,他乔装而来,现在正在上京城内。”
第95章
因着虞娄灭亡了大庆,掳掠了不少大庆工匠一起北迁,现在虞娄的手工艺品、冶炼品等制造技术都有了极大的提升,虽然若论精致程度,与南庆还是有着不小的差距,但对于蒙古等国等北方国家来说,前往南庆着实不便,虞娄的产品,在整个北境就是最好的。
蒙古国老祖宗要过寿,蒙古王子来虞娄采买贺礼,倒也不足为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