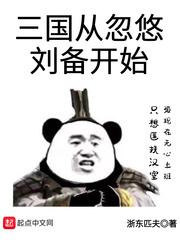笔下文学>帝姬不远嫁完结金手指 > 第13章(第1页)
第13章(第1页)
>
纯懿只以为他会继续纠缠,却没曾想得到了她老老实实的回答,延陵宗隐似乎便已心满意足。
他后退几步,对着纯懿微一躬身,是一个很简单的虞娄礼节,却被他做的肆意潇洒,分外好看:“帝姬多休息,可千万不要着了风寒。若是起了高热……”
他停顿,唇边笑意更深,只是怎么看都似带着些不怀好意:“全身都烫,尤其……那我可就不好控制了。”
他这话说的古怪,纯懿没太听懂。她也并不对此感到好奇,只对他点头:“承将军吉言。”然后便转身要走。
只是估计是脑子不清醒的缘故,刚走了一步,她又鬼使神差般停下脚步,回过头去,少见地主动去直视延陵宗隐的漆黑眼眸。
“我成亲了。驸马与我是青梅竹马,我们的感情极好。”纯懿没头没脑地道,“就算不说这个,我们大庆娘子都是从一而终的,绝不会做对不起郎君的事情。”
“我知道。”延陵宗隐没对她这突如其来的剖白露出一丝疑惑,微笑点头,神情自若,仿佛那日看着她与陆双昂,语气冰冷、眼神狠厉的人不是他一样,“我们虞娄风俗倒是有所不同,喜欢哪个女人,抢来就是。若是这个女人有主,那男人要是识点眼色,还能留着一条命在,去偷别人家的花,总是更刺激的。若是没有点儿自觉……”
他侃侃而谈,像是只是由着她的话头,为她介绍虞娄风俗一般:“……杀了做肥,还能让花儿开得更鲜艳一些。帝姬说是不是这个道理?”
不待纯懿露出些惊愕之情,延陵宗隐已经颔首,摆出一副送客的表情,还不忘再次叮嘱:“帝姬可不要起了高热啊。”
一语成谶。纯懿还没走回屋子,就觉头重脚轻,差点一头栽倒在地上。紫节和女使们将她连拖带抱地送回屋子,纯懿的额头已经滚烫,脸颊通红,甚至都有些神志不清了。
一直到晚上入睡时,她仍还烧着。
那个梦却没有因着她的虚弱而放过她。
还是被牢牢捆缚的双手,还是被强力压制而动弹不得的身躯,纯懿再次梦到了那个男人。不同的是,这一次,她的身体甚至比那个男人火热的身躯还要滚烫,虚弱无力地任他为所欲为,似乎也更轻易地勾起了男人的兴致。
他黑眸被暗色所染,看着在他身下蹙眉叮咛的小娘子,感受着她柔滑却灼热的肌肤,除了来自本能的冲动之外,还多添了来自他劣根中的几乎难以压制的毁灭欲望,想要弄疼她,让她哭求不绝,让她为她的所作所为付出代价,让她不甘不愿却不得不彻底臣服。
他手下就有些失了力道,在她滚烫的耳边恶狠狠地低吼:“不是说了,不要起高热,不然我会不好控制吗?”
纯懿紧闭着双眼,全身因为恐惧而战栗着,深陷在这个梦中,无法挣脱。
第二日早上,纯懿的高热倒是退了,可全身却乏困无力,几乎连起身都做不到。可想到母亲的药还在延陵宗隐手上,纯懿咬着唇,强撑着无力的两条细腿,哑声吩咐紫节帮她梳妆。
紫节昨夜又睡得很沉,一晚上都没有醒。她恼恨自己实在不称职,又心疼纯懿的情况,苦口婆心地劝她今日就不要去了,延陵宗隐虽然看着冷厉,但为人似乎还不坏,她去帮她解释一下,想必他也不会生气。
事关母亲,纯懿却一点儿风险都不愿冒,仍坚持着要亲自过去。
两人正拉扯着,一位正殿女使却忽然跑来,满脸喜色:“帝姬,温姆让奴来回禀,延陵将军已将今日的药送入坤宁殿,温姆一会儿就服侍娘娘服下。帝姬昨夜辛苦了,今日就不必起身,好好休息便是。”
说完,又急忙补充:“哦,对,最后一句是延陵将军吩咐要转告帝姬的。”
听说药已经送到母亲那里,纯懿正松了口气,虚弱躺回床上闭目调息,可待听到最后一句,她心里一动,剎那只觉身上更疼了。
这种疼痛,似乎却与发热引起的疼痛不太一样,可具体哪里不一样,纯懿又说不太清楚……
想到那个近来如影随形且愈演愈烈、越发真实的可怕梦境,纯懿还是没法安心休息。她命人搬来一副黑檀木嵌螺钿的六折屏风立在床前,吩咐道:“派个人去前面守着。等前朝散了,请汴京府尹来一趟。”
然后又问紫节:“这两天都是谁在守夜?我要问几句话。”
见过了汴京府尹和值夜宫人,纯懿倚靠在床头,觉得仅存的力气也都被耗尽了。所有的一切都在证明,那只是一个梦,可能因着她最近频繁见到延陵宗隐,重又勾起了她深埋心底的恐惧,所以让这些梦过于真实,从而使她产生了幻觉。
一个已经确定死去的人,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再活着出现。一个根本没有来过汴京的人,也无论如何都不会与那件事有所关联。而一个虞娄王子,更是无论如何也不可能越过重重宫闱,在深夜摸进皇后的坤宁宫却没有惊动任何人。
只要不见到延陵宗隐……至少少见他一些,想来这些奇怪的梦境,就会渐渐消散吧。
纯懿躺在床上,将紫节偷偷递给她的东西牢牢黏在指上,这才敢合上双眼,祈盼着今日能有一个好眠。
第8章
熟悉的被束缚、被揉捏、被啃噬的感觉袭来,将本就不敢安心入睡的纯懿惊起。一片迷蒙之中,她仍不能辨认这到底是过于真实的梦境还是伪装成梦境的真实,只能尽力抬起双手,轻搭在男人坚实的肩膀上,然后顺着他肌肉贲张的手臂一路下滑,最后落于他的手腕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