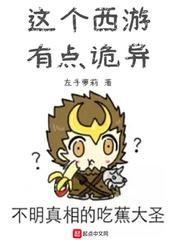笔下文学>权宦上位手册全文阅读 > 第174章(第1页)
第174章(第1页)
>
荣蓁就那么看着她,直让她心里有些发慌,荣蓁轻飘飘道:“所以,你们吴县令就是这么成全我的?只给了三成,让我无法完成这样一件大事。”
主簿来之前早已经想好了说辞,“荣大人,您也是房州官员,应该也知道咱们房州不是富庶之地,这些银子已经不少了。余下的一些银子,吴县令有意留着赈灾用,您要做的事是大事,吴县令自然也是一样。”
这分明就是两人合计好的,屏风后,秦楚越咬紧了牙,她恨不得将那两人撕成碎片。
荣蓁闻言,露出嘲讽笑意,“是吗?”
可下一瞬,还未瞧见荣蓁如何动作,主簿已经被荣蓁扼住了脖子,后退几步抵在了门上,她紧紧抓住荣蓁的手,似乎想挣脱开来。
荣蓁的声音如同冷刃一般,“这种被人握住命脉,喘不上气来的感觉是不是很难受?你是觉得我可以被你们肆意耍弄吗?”
主簿摇着头,脸色涨红,口中说不出话来,可眼神里都是哀求,面对生死,少有人可以从容以对。
荣蓁的手一放,她便跌倒在了地上,抚着自己胸口,不停喘着气,还未站起,荣蓁抬脚踏在她的身上,睨视着,如同俯视蝼蚁一般,“想做吴县令的左膀右臂,我不拦着你,可你若是想算计我,最好想清楚,你帮她得到一切,自己的命保不保得住?我有许多方法可以让你求生不得求死不能。”
荣蓁踩在她胸口,主簿只觉心都要被碾碎了,求饶道:“我不敢……”
荣蓁道:“回去告诉你主子,我要做的事,她最好不要阻拦,否则我也不知自己会做些什么。”
荣蓁话音一落,便松开了她,主簿扶着门爬了起来,跌跌撞撞奔了出去。等人走了,秦楚越从屏风后出来,恨声道:“这样还真是便宜了她们!”
荣蓁看着手中的印信,“如今我手上只有三成的银钱,那番话即便是能够威慑住她,只怕也只能再讨回两成。”
秦楚越看着她,道:“这本就是做给皇帝看的,其实若能有五成银钱,便也足够了。”
荣蓁面色沉了下来,“你以为我做这些只是为了在陛下那里邀功请赏,兴修水利之事若是敷衍,等到水患真的到来时,那便不是天灾,而是人祸。”
秦楚越忙道:“我不是那个意思,我只是……”
秦楚越话说到一半,又觉得解释也是牵强,她方才的话脱口而出,却未必没有那么想过。
秦楚越看着荣蓁的脸色,“那这钱财若凑不齐,我们应该如何做?”
荣蓁道:“我会想办法。”
离开之前,秦楚越回身看着荣蓁,“其实我倒是觉得,那个将她踩在脚下的你,才是真实的你。”
荣蓁语声极淡,“她已经触了我的逆鳞,若是还不知反抗,那便与行尸走肉无异了。”
而最后也如荣蓁所料那般,吴县令又让步一些,而主簿再见了她,眼神中总会带着一丝畏惧。
荣蓁这几日早出晚归,慕容霄问她白日都做什么,荣蓁却总是不肯告诉他,他想起一人,天色将暗时,将人堵在了门外。
慕容霄看着满身疲惫的秦楚越。问道:“你和荣蓁究竟在做什么?难道也要瞒着我吗?”
秦楚越对慕容霄并无敌视,知道他也是关心荣蓁,便同他把事情来龙去脉说个清楚,“她不愿你牵扯进来,她说这本就是房州的事,钱款也应由房州的人来出。我虽有些钱,但也不过是杯水车薪。所以这几日她便与我一起去商贾家中拜访,让她们对兴修水利之事出一份力。”
若是轻易便能成功,秦楚越又怎么是这副模样,慕容霄道:“那些商贾不肯吗?”
秦楚越直言道:“商人重利,这样有名无利之事,她们哪个肯t做?”
慕容霄没有再问,他转头便离开了,秦楚越在他身后道:“你可莫要说来找过我,免得被她知道了,又要同我兴师问罪。”
荣蓁在家中未见慕容霄的身影,刚要出门去寻,便见他提着酒菜回来,荣蓁眉宇间舒展开,“我还以为你又有急事回姑苏了。”
慕容霄牵着她的手,“你放心,我舍不得走。即便是要走,也定会同你好好说一声,不会不告而别。”
荣蓁看着他提着的食盒,“去买了什么?”
慕容霄温柔地看着她,“总是吃我烧的菜,怕你会厌烦,便去城中酒楼里弄了些酒菜回来。”
荣蓁笑道:“我何时说过厌烦?莫要冤枉我。更何况,你当初做菜的本事不怎么好时,我不也全吃下了吗?”
慕容霄其实是心疼她,“不止有这些酒菜,你这几日这样累,我已经备好了热汤,可以沐浴解乏。”
荣蓁捏了捏他的手,“你可真是体贴入微。”
两人用过晚饭后,荣蓁靠在浴桶中闭目养神,她脑海中还思索着白日之事,慕容霄推开门将衣服送过来,见她眉头紧锁,他将衣衫放到旁处,走到荣蓁身后,手指轻轻在她的太阳穴处揉按着,“有什么烦心事大可以告诉我,即便我不能替你解决,至少也不闭闷在心里。”
荣蓁按住他的手,仰头看着他,慕容霄的手托在她的下颌上,荣蓁道:“也不是有心瞒你,只是不想让你一起搅进来,劳心劳神。”
慕容霄轻声道:“人常说患难与共,难道你之前同我说的那些话,都是诓我的?”
荣蓁听他这样说,心里已经有了猜测,“你知道了?”
虽未明说,但慕容霄知道她指的是什么,“其实这银子于我不是难事,你只需同我说一声便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