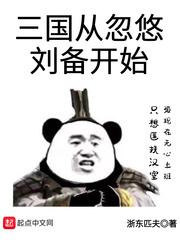笔下文学>表姑娘出嫁后被疯批权臣强夺了免费阅读 > 第157章(第3页)
第157章(第3页)
他也顾不得和她较劲,小心翼翼的扶着她趴好,把软枕给她调整了一下,唯恐牵扯到她的伤口。
他沉着脸,语气难得的严肃:“你身上伤重,不要乱动,伤口撕裂了更难痊愈了。”
婉若趴在软枕上,拿后脑勺对着他,一句话都不想和他说。
他拧着眉,下意识想教训她,一看到她后背的伤,又什么也说不出来了。
他抿了抿唇,语气有些干巴巴的:“好歹把药先喝完。”
“我不想喝!”
他放轻了声音:“那晚一点再喝?”
她不理他了。
他深吸一口气,将药碗放下:“那你先睡会儿。”
她依然不说话。
他也没再说话,屋内渐渐的安静了下来,陷入了漫长的沉寂之中。
沉寂到让婉若以为,他已经走了。
她趴在枕上,悄悄扭过头,却看到了依然守在床边的男人。
他沉沉的看着她后背的伤,那双向来从容又孤傲的眸子里,装着她从未见过的黯然和破碎。
他注意到她的视线,收敛了眸光看向她,她立即转回头,将脸颊埋进软枕里。
只是那股酸涩好似在心口蔓延开来,好像更难受了。
接下来几日,谢羡予当真再没去上朝了,他寸步不离的守着婉若,甚至连门都不出。
他也没再允许任何人进松鹤园,大夫人听闻婉若从凤仪宫回来就病重,前来探看,他也只应付过去。
其他人等连门都进不了。
三日后,苏言再次登门了。
“我全部查过一遍了,得知你和齐王之事的人,除了你爹就是其他安插在朝中的几个重要暗线,那几个人近期没有和宣王来往的任何迹象。”
谢羡予双眸微眯:“我爹有?”
苏言神色严肃:“京中的暗探查到的消息,谢相礼在年前亲自去宣王府送过年礼。”
“宣王府在明面上与谢家本就是一条船上的人,送年礼也是谢相礼分内之事。”
“这的确算不得什么,可他送年礼的日子,恰好是你的密函送回京城的第二日。”
谢羡予眸光一凛。
苏言道:“此事说大不大,说小不小,有可能只是巧合,也有可能,问题就出在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