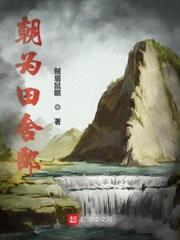笔下文学>绍宋在哪里可以看 > 第五十章 忽暗忽明(第1页)
第五十章 忽暗忽明(第1页)
十月中旬发生在汾水畔的这场战斗毫无疑问是一场击溃战,而且是一场骑兵之间的击溃战,而且还是一场道中相逢、以少胜多的骑兵击溃战。
这种战斗,想要扩大战果只有战后迅速追击,或是趁势造成伤亡,或是趁势夺取一些战略要地。
否则,这一战只能说是挫败了金军偷袭河中的图谋而已。
当然了,这已经很了不起了,但韩世忠的性情摆在那里,绝不可能就此罢休……故此,其人一冲成功,只是回身与解元交代一句,便即刻催动背嵬军逆汾水向东追击不停。
但是真的很难造成金军的大溃散。
双方都是骑兵,都是仓促行军抵达战场,然后都得以趁着战事使马匹稍歇,此时你追我赶,根本不可能趁势追上。更兼金军骑兵数量太多,之前下马作战的数量就很多了,主动也好被动也好,也都是给后方金军的撤退争取了整备时间。
某种意义上来说,撒离喝其实也算果断。
而这日晚间,韩世忠因为天色下令停止追击的时候,却果然已经进入到了稷县境内,也就是他的兄弟解元家乡所在,完全称得上是说到做到了。
不过,可能是因为需要随后清扫道路,收罗掉队士卒的缘故,解元比韩世忠晚了近一个多时辰才抵达韩世忠屯驻的村庄。
入得庄来,看到村庄空空荡荡,只有几个年迈老者,这让见惯了类似事情的解善良难得有些烦躁不安起来。
兄弟二人相见,篝火旁正在擦拭自己长矛的韩世忠率先开口:“善良,这地方是你家不?”
“不是。”解元摇头以对。“我家路上已经过去了,是个山岭坳子,我下马瞅了眼,早就荒废了。”
韩世忠点点头,再问:“如何?”
“不好。”几十年兄弟,解元当然晓得对方的意思,便再度摇头。“汾水如今已经变浅了……而且中午太阳晒得也不是太凉,许多散乱下去的金国骑兵,有马的直接抱着马脖子,没马的直接解了甲凫水过去了,也就是比那次铁岭关南边稍强……估计就是勉强过千的斩获。”
“不错了。”韩世忠丝毫不以为意。“过河一旬,连做三仗,斩获三四千了……生平之大胜了,还指望啥?!”
解元点头应声:“关键还是河东城,此战后金军不能救河中……那温敦思忠和他那个万户就插翅难飞了。”
“那便是一个半的万户。”盘腿坐在地上的韩世忠给自己长矛套上套索,昂然相对。“天下人便该晓得为何是我韩世忠天下无双了?”
“五哥。”解元也不坐下,依旧在篝火对面正色劝解。“这一战是国战,咱们三十余万,金国也有二十个万户加上什么燕京新军,几千斩获、一个万户,不过是大战先挫锐气,万万不能倨傲失态。何况,拔离速尚在前方没有退走的意思,便是河中府也尚未有定论。”
“我知道。”韩世忠含笑以对。“不过,这一回他既受挫,留着也没意思了,正该趁势将他驱走!”
“我已经派人去寻许世安、陈桷他们了。”解元立即应声。“明日应该便能抵达,咱们届时汇合部队,大举渡过汾水,攻取河北面的稷县县城,再进逼绛州州城,做出一副要顺着汾水向北断金军后路的姿态,拔离速要么分兵渡河来与拒我们,要么直接滚蛋。”
“太慢!”韩世忠摇头以对。
“五哥有了别的主意?”解元略一思索便晓得对方意思了。
“你看那座山如何?”韩世忠努嘴向南。
解元诧异回头,只见尚有余光兼月光的暮色中一排山岭轮廓清晰,正黑洞洞蹲在那里,其中一座挨得比较近的,明显高度、宽度超过其余山头,应该正是韩世忠示意所在……但解元仍然不解。
“想要撵走拔离速,最好是趁热打铁。”韩世忠见状从容解释道。“趁着他摸不清白日这一场到底有多少伤亡,我们有多少兵力的时节,今晚稍作歇息,即刻再度奔袭过去,尾随撒离喝的溃军敲他大营,逼他撤兵转回临汾……可咱们兵少不说,若是仓促再往前去,后勤也不足,一旦受挫,届时又天亮,反而要出大事……”
解元颔首不停,不要说自古以来,便是他们二人亲身经历过的乐极生悲之事就数不胜数。
“不过,所幸敌营与铁岭关只隔着一条小小浍水,若李彦仙能提前知道咱们想法,与我们一起合力出兵,便是不成,咱们也能从容进退。”韩世忠继续言道,却是道出了自己的的想法。“所以,我想仿效当日马扩举止,点火烧山,以作威吓,也当联络。”
解元怔了一下,本能摇头:“马总管当日并未烧山。”
“一个意思。”韩世忠嗤笑以对。“大家一下午冲了六十里,正该歇息,难道还要让大家临时造火把,再上山不成?”
解元点了点头,一声不吭,转身离去。
“你去哪里?”韩世忠诧异相对。
“去烧山。”解元停都不停。
“不歇一歇吗?”韩世忠愈发不解。“况且烧山这种事情,哪里要你一个副都统过去?一个都头足够了!”
“五哥。”解元终于在相隔几十步的距离停下,回头相对。“你这个主意极好,正是眼下最妥当的计策,不可能不去做的……但你看沿途村庄,全都空空荡荡,人都到哪里去了?”
韩世忠微微一怔。
“我没有阻碍军事的意思。”解元继续言道。“但我是副都统,又是本地人,只要告诉下面军士此事,再亲自往山下一站,他们自然会先尽量驱赶山中百姓,然后再烧……否则以他们眼下的疲敝,怕是直接一把火了事,到时候又如何呢?”
韩世忠没有言语,只是点了下头,便低头去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