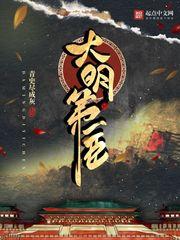笔下文学>今夜沉沦短剧免费观看全集 > 第3474章寻常快乐(第1页)
第3474章寻常快乐(第1页)
正是如此,一旦病了,便会来势汹汹,症状会非常严重,也幸而我有真气护体,不然非得在医院躺上几天不可。
其实偶尔生一次病还可以清除体内的病毒和有害细菌,特别是发烧的过程,人体的免疫系统会倾泻而出,对于脏器会进行彻底的消杀,比如像癌细胞,其实不用觉得可怕,正常人的体内都会存在有害细菌,而发烧时正是防御机制开启,与其博弈的方式,最终会刺激白细胞的生成量,从而加强免疫系统的抗病能力。
简单一些来理解,就是人体代谢和净化的过程,就如同做手术清除毒瘤一样,可是生病会让人变得不安和慌乱,因为在失去意识的那一瞬间,我感觉自己的灵魂似乎正在抽离,它渐行渐远,直到我完全没有了知觉。
怕死吗,很多人也许会大义凛然地说不怕,然而真当死亡降临,自己能切身体会之时,深埋在心底的恐惧便会控制不住涌现而出,你会变得失去理智,更是惊惧窘促。
我忽而想到了洪琳,不知为何,我很想让她陪在身边,或许是她能给我为数不多的温暖,让我孤寂的心可以得到抚慰。
想到这里,我忙不失迭地拿出了手机,在虚弱没有思考能力之时,我惊觉自己居然还能清晰地记得洪琳的号码。
电话很快接通,洪琳清脆的声音传了过来,“小严,你终于想到给我打电话了,在忙什么呢?”
“我给你打了好几个电话,但是都关机了,你该不会一直在做实验,把自己关起来了吧。”
我如今听着她的埋怨,却觉得异常悦耳,“琳姐,我,我生病了,难受得很。”
“啊,怎么会这样。”洪琳立刻变得紧张起来,“小严,你在哪儿,洋房吗?”
听了这话,我果然得到了宽慰,“感冒了,我在洋房附近的站台边……”
这一次病得突兀,说出这番话像是耗尽了我全身的力气,弱不禁风的,像是随时要倒下一半。
这时,洪琳问道:“那个站台是不是在你家路口拐角的地方?”
我嗯了一声,随即便挂断了电话。
洪琳是个聪明的女人,她应该能够明白我打这个电话的用意,相信要不了多久就会来到我的身边。
靠在树上我得以喘息,仍然舒服了不少,至少我的视线变得清明起来不再眼冒金星。
我站的地方正好是一个交通枢纽,很多路人在我身边行走匆匆,公交车一辆接着一辆地停在我的旁边,仿若我和周边的一切都格格不入。
我坐在花坛边好整以暇地看着人来人往,突然有一对年轻的夫妻他们骂骂咧咧地走了过来,女子的怀里还抱着孩子。
走近了之后,我听到那名女子正在骂人,说出来的话极其刺耳,“这孩子就跟我一个人生的似的,你压根就不管。”
“早知如此,我还不如给你戴个绿帽得了。”
男人一听脸色变得很是难看,但似乎在隐忍什么,唇角蠕动了半天才憋出一句话来,“你就不能消停一些,孩子还在身边呢!”
女子恶狠狠地瞪着男人,“真是烦死了,过的叫什么日子?”
男人没有回应,而是很贴心地将孩子抱了过来,脸上带着真诚的歉意。
虽然这对夫妻正在发生矛盾,然而我却觉得异常的顺眼,家长里短吵吵闹闹不就是最幸福的日子吗?
可怜这最寻常的一幕,都很少经历过,更别提一家三口欢欢喜喜地出来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