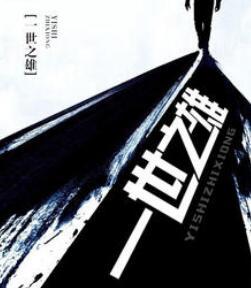笔下文学>鸿源的意思和含义是什么 > 第100章 漫长的旅程 丽丽和乌达尔岑浩聊北大(第1页)
第100章 漫长的旅程 丽丽和乌达尔岑浩聊北大(第1页)
船从斯里兰卡科伦坡出发,下一段的航程更遥远。丽丽想起在宿舍里和群莉、小芹还有另外几个同学通宵卧谈,对两个姐妹的思念又压上心头。尤其是群莉,也不知道身体恢复得怎么样了。
“你又发呆了,会不会担心下一段耗费时间长?”乌达尔问丽丽。
“我想群莉和小芹了,不知道她们忙什么。群莉身体恢复得怎么样。”丽丽轻声说道。
“那她俩一定也在想你,我们的谚语里是这样说的。当你思念一个人,他也一定在思念你,因为你们是朋友。”乌达尔微笑着说。
丽丽点点头,见岑浩也坐起身,冲他微微一笑。现在,岑浩已经是丽丽心目中的才子了。
“你别听他胡说,他哄你的,这话我听说过,但绝不是乌干达的谚语,是哪个国家的,我一时也记不起来了。”岑浩说道。
丽丽嗔怪地瞪了乌达尔一眼,还“哼”了一声。乌达尔两手揣进裤兜里,靠在床板上,嘻嘻地对丽丽笑。这姿势,这派头怎么越看越像吕一鸣呢,丽丽微微皱了一下眉头。
这次邱教授去川大交流新诗,丽丽从头至尾都听了,她自己对新诗不是很懂,但前两届中文系的学长们出了一群一群的诗人,感觉他们那种有激情的人,很有特点。她知道吕一鸣一直都是热衷诗歌的,顾城那句“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她追求光明”,就是吕一鸣最先告诉自己的,的确不错。在川大,丽丽录下了邱教授的课,这一路上听了几遍,觉得理论性强,给自己写论文提供了范本。
“乌达尔,你什么时候到北大的?去年改造大饭厅的时候,你在吗?”丽丽忽然问。
“在,还参加过义务劳动呢。”乌达尔似乎来了兴致。
“我知道,东面墙上后来写的口号是:‘勤奋、严谨、求实、创新’,对吧?”岑浩说道。
“你去过北大?没听你说过。”丽丽目光中流露出惊喜。
“还不是给他当走卒。”岑浩指指乌达尔,笑着说道。
“嗯,那是我第一次去北京,他说跟我一起去看看皇帝睡觉的地方。”乌达尔也学会嬉皮笑脸了,还是刻意逗笑自己,丽丽想着。
的确,八十年代,是一个转折的年代,人们有着共同的集体记忆。那个特殊年代的青年人,从长久封闭在一眨眼间就面对开放,他们发出“寻找自我”的呐喊。
“七六年,我也去过一次北京。”岑浩低声说道,声音很凝重。
“我是从那以后,才爱上了现代诗。之前,我认为现代人写的再好,也写不出古诗的水平。那以后,我知道了,写诗的激情也来自愤怒,悲伤。”岑浩说着站起来,从箱子里拿出一本杂志,递给丽丽。
丽丽接过一看:《今天》。她更加惊喜了,这本杂志吕一鸣也给过自己。
丽丽霍地从铺位上站起来:“你也有这本杂志?”
“是啊,我喜欢北岛的诗。还有你们北大几个学生的诗也蛮好。当然,我也说不出好在哪里。”岑浩说道,显得有点儿不好意思。
他又想抽烟了,浑身上下摩挲着。乌达尔帮他从抽屉里拿出了一包烟,和打火机。于是三个人一起走到甲板上,面朝大海畅谈万里之外的京城。
去年,年久失修的大饭厅改造,在校学生轮流参加义务劳动,改造过的餐厅依然条件简陋。但大家最开心的是,演电影的地方大了许多。一旦放外国电影,座位占满了不算,很多学生自带小凳子,坐在走道中间,整个饭厅塞得满满地。但就是这样简陋的条件,与室外嘈杂声“混响”的影厅,却有最专注的观众。全场电影厅内只有影片的声音,和放映机转动的声响。十几年间,这里是票价最低廉,环境最差,却品味最高的影厅。
“乌达尔,你们乌干达有电影吗?”丽丽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