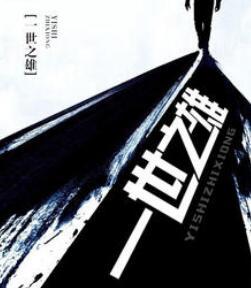笔下文学>重生七零糙汉军官霸宠娇娇知青 > 第494章 屋漏偏逢连夜雨(第1页)
第494章 屋漏偏逢连夜雨(第1页)
刚一出去,小张就被迎面刮来的冷风噎了一口气,紧了紧大氅,前方十几米的地方,宋尧军正笔挺地站在那,跟人交涉。
边防哨所的老战士,引着一位牧民介绍:“老乡是来求助的。”
牧民穿着宽大的袖袍,五彩斑斓,充满异域色彩,黑黢黢的脸上,神情十分焦急。
“今早上我一起来,发现家里的羊圈破了个洞,羊也少了好几头,家附近能找的地方,我都找遍了,可连根羊毛都没找到。
这天寒地冻的,羊丢在外头,不是饿死冻死,就是被狼叼走。娃他娘还指望着卖羊的钱看病呢,这可咋办啊。”
说着说着,牧民就将手从飘曳的袖袍中伸出来抹眼泪。
这边防气候恶劣,人烟稀少,多以游牧为主,而现在又是枯草期,几只羊几头牛就是全家的希望,眼下跑了好几只,自然着急。
“老乡您别着急,先跟我们说说,您一般去哪里放牧,尤其是远一点的,我们肯定会帮你把羊找回来的。”宋尧军语气坚定地说。
牧民感动地眼泪汪汪,上前一步握住宋尧军的手,动情地说:“真是为人民服务的好同志啊,有你这句话,我就把心放在肚子里了……”
接下来,他就指出了几个经常放牧的地方。
宋尧军一愣。
边防哨所的老兵以为他刚来没多久,对地方还不太熟悉,自然承托了介绍的职责。
牧民欣喜若狂地在前边引路。
宋尧军却有些疑惑地想,边防苦寒,风刮在脸上跟刀子一样,反正他到这里见到的人,无一不是手跟脸都黑黢黢的,布满了沧桑。
可这牧民刚才握住他手的时候,并没有想象中那么粗糙皲裂,反而十分光滑,而且虎口处似乎还有老茧。
难不成这老乡平时很注重保养?
……
宋禹晏最近实验十分不顺利。
一个简简单单的处理实验,连着做了三次了,都没成功。
第一次是组培瓶的盖子被人拧开了,空气进去,长了杂菌,作废。
从头再来,第二次,结果培养室里的灯,不知道又被谁给关上了,他明明都提前写了便签,他需要光暗处理(16h8h),灯光的条件变动了,那么变量也就不唯一了,还怎么接着往下做?
第三次,他意识到,肯定是有人故意给他使绊子,既然如此,那他就经常在组培室里呆着,守着他的苗子不就行了?
而这一次也不辱所托,他终于是种出来了预期的表型,结果等他取完了样,正准备测数据的时候,仪器突然坏了。
实验做不成了不说,还被人扣上了一顶屎盆子,他的死对头,直接闹得众人皆知,说是他把仪器弄坏的。
简直要命了,他才刚把仪器打开,怎么就成了他操作不规范,把从国外进口的仪器给弄坏了?
他可连用都没开始用呢!
他拼命解释,肯定是上个使用的人弄坏的,但死对头不乐意,说按照实验室规章制度,每个人借仪器的时候,都要当场跟负责人检验一下,仪器有没有损坏,是否还能正常使用。
谁让他太傻白甜,太相信实验室的同门们都是一群善良有良知的人,就没检查,直接拿回来用了呢,如今人在家中坐,锅从天上来,是他活该,是他应得的。
不就是赔偿吗?
他堂堂宋老三,怎么可能连这几万块钱都拿不出来?简直笑掉大牙。
但还是好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