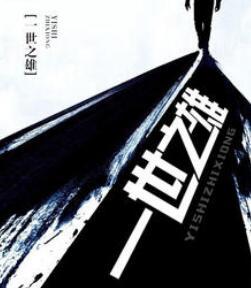笔下文学>渡春宵姜念最后和谁在一起了 > 第305章 缘木求鱼(第1页)
第305章 缘木求鱼(第1页)
自打两年前,一个不孝的罪名安在他身上,他这高台上的明月早就跌了。
加之当初假意接近江陵县主,却在临江王事发后对之弃如敝履,叫京中女儿对他也变了口风。
薄情寡义、攀高踩低,这些都算是好听的。
“我只求身侧之人懂我,仅此而已。”
将沈渡剖开来,姜念发觉,他与自己全然不同。
“也就你受得住,”她玩笑似的说着,“换了我,只觉得太累。”
身边男子许久没出声。
等她默默扒下半碗米饭,他才又缓缓开口:“倘若……”
“沈渡。”
一如他云锦着身那日,姜念选择了打断,“这汤还不错,你替我盛一碗吧。”
沈渡没再往下说。
修长白净的手,不提笔写字,替她盛汤都格外赏心悦目。
姜念像是不知晓他的心思,近乎残忍地念叨着自己的往后。
“我去年刚置办了一间作坊,几十架织机,等手中有些盈余,便想着再置几亩田地养桑。也不知到那时候,你量到我那儿没有。”
她清楚知道自己的往后,在苏州、没有他。
这顿饭,沈渡自己没怎么动,一直在替她布菜。
姜念看不下去,便只能自己吃完,反过来给他也布一回,劝着他多少吃些。
夜里要住的那间房并不陌生,只是从前养病,她也没站在此处好好看过。
那顶织了折枝海棠暗纹的纱帐,姜念看多少次都觉得好看极了。
身后男子跟着她迈过镂花月洞门,见此情境又说:“二月里,宣平侯府的海棠想是开了。”
“那我们明日去看吧。”
只要不涉及去留,她是特别好说话的。
沈渡也决定,就如从前那般,暂时抛却往后种种,且着眼当下吧。
姜念总觉得,这一夜带着些心照不宣的默许。
恰如城郊银汉桥下,她们躺在一处看星陨,沈渡吻了她;今夜准他躺在身侧,实则也是一种默许。
她还从未见过他褪去外衣的模样,总以为他身上书卷气浓,身形也颀长清瘦,而今只着贴身里衣,隐隐显露的胸膛告诉她,沈渡一点儿也不瘦。
姜念躺在里侧,锦被覆住半张脸,露出一双眼睛去瞧他。
沈渡的吻便落在她眼角,很轻,一下一下移至眉心。
“明日就要回去吗?”再开口,清润的声线低哑。
姜念脸都是烫的,告诉他:“你若想我多留几日,也不是不可。”
他那只白净的手伸过来,拉下她高高盖着的被褥,终于毫无阻碍覆上她面颊。
或许是自己面颊太烫,他指尖是凉的,昔日温和的眸光却滚烫一片,暗暗克制着占有的野心。
只是他不甘心,到今日他也位高权重,分明也能站出来争一争她,触碰她,却还是名不正言不顺。
对此,姜念只觉得煎熬,是钝刀子割肉的疼。
她破罐子破摔似的,勾住他颈项便吻一口,看着他清隽面上蔓开一片红。
却没有如她所想被勾动,沈渡俯下身来,将她紧紧抱住,几乎可以说半压在她身上。
他很难过,姜念能够感知到,于是她也难过。
“真的想好了吗?”他声调不稳,“你真的要,放弃我吗?”
姜念只能说,她觉得很可惜。
在苏州的那两年,她实在是太喜欢了,她总要先选自己喜欢的地方,再从合适的人中挑一个喜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