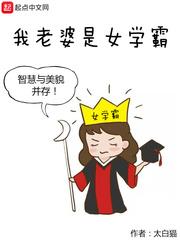笔下文学>我是你的人 我不是人 > 第 20 章VIP(第2页)
第 20 章VIP(第2页)
人类的嘴唇柔嫩温热,啵啵两下,直亲得时夜生的酥麻发软,表皮都荡漾起波纹来了,哪还听得到他在说什么?因此只有嘴上诚心认错,心里死不悔改。
今天的工作任务很重,徐久被安排去清洗实验器材。
又要穿上厚重的防护服不说,试管和蒸馏瓶上全糊着焦油一样漆黑的玩意儿,强力的清洗试剂根本没什么用。他浸泡了三趟,洗得额头直冒汗珠,上面还是腻着一层油乎乎的膜。
不是人干的活啊,他叹口气。
徐久倒没觉得有多累,得益于昨天晚上被强灌的经历,他目前还体力充沛,精神也饱满。其他人可没这么好运,全累得气喘吁吁,哈出的白雾与水珠将面罩染得蒙蒙一片,又不好擦,只能就这么忍着,站得腰酸背痛,洗得手臂僵直。
正在他发愁的时候,水母偷偷地挨近他耳边,用只有他能听见的音量悄悄怂恿:“我帮你。”
徐久无奈道:“唉,这个不行的。”
六号的力气大得吓人,脆弱的玻璃器皿,徐久还真不敢让它上手,只怕它轻轻一碰,这些奇形怪状的小玩意儿就得碎成齑粉。
然而水母并不放弃,防护服从头穿到脚,是无缝的一整套,也不知它找到了哪里的缝隙,居然把触手伸了进来,不屈不挠地拨弄着徐久的耳垂。
“我帮你。”它执着地说。
“都说了这个不行……”痒痒的,徐久忍不住抬起肩膀,试图把耳朵边上捣乱的小触手赶走,“这些东西禁不起你的力道,你一下就碰坏了,到时候我还要赔……”
“不会的,”水母坚持,“你看。”
手里的试管刷突然变重了。
徐久低头一看,他讶异地发现,手里的工具正如同活物一般,渗出半透明的胶状粘质,有如坚韧的软体,缓缓流淌到刷子的尖端,将其包裹成一块儿。
很快,他手里就晃动着一根弹性十足,尖端还可以随意弯曲的水母触角。
徐久:“?”
他赶紧把它沉到水里,警觉地朝周围看了一圈:“喂!万一被人看见可怎么办?!”
“不可能,”时夜生说,接着催促,“我能帮你。”
徐久将
信将疑地挥了挥刷柄,触角在他手中颤颤巍巍,不住乱摇。
……总感觉这是什么造型诡异的仙女棒,就还蛮奇怪的。
但也没别的办法,他试着把刷子探进蒸馏瓶,小心谨慎地晃荡了一圈。
——效果着实惊人!也不知道水母的粘液有什么奇异功效,那些难缠的焦油物质立刻便被轻松地溶解滴落,再拿淡水一冲,瓶壁清澈透明,简直洁净得发光。
徐久的眼神也跟着发光了。
他如获至宝,就像拿到了什么新奇的玩具,挨个在一堆形状刁钻的玻璃器皿里胡乱钻洗,尝试测试这根小刷子的威力。时夜生则心情愉快地盯着他,全身的口腕来回轻飘飘地摇摆。
见没有人注意到自己这边,徐久甚至开始将触角弯成各种轮廓,再浸着清洁剂,偷偷地在空气里挥出奇形怪状的泡泡。时夜生也纵容地用身体笼罩住他,微妙地扭曲他周身的光线,让监控器和人类的肉眼都无法观测到这里的真实情况。
这明明只是件微不足道,小得不能再小的事,但人类却能从中汲取到万分隐秘的快乐,并像个孩子似的窃喜。
时夜生突然意识到一个事实,它开始觉得,人类可以向自己提出任何要求的,只要是从他的嘴唇中吐出的愿望,它都会非常高兴地令其成为真切存在的现实。
也许它的心肠是比过去软弱了一些,但如果人类没有得到他想要的一切,那将是一种耻辱,因为那意味着它无法妥帖地供养这个如此珍贵、完美的生物。
——那就是它彻底无能的佐证。
时夜生仔细地瞧着徐久,它看得越仔细,越专注,心中的冲动就越是明显。它现在就想冲出去,在这个强敌环伺的地方大开杀戒,咆哮着挑战所有对手,以此来展示自己的强力与雄壮。吞噬,杀戮的狂宴过后,它会成为唯一屹立不倒的主宰,接着,它就把这份胜利奉送给人类,再亲自用最丰美,最富饶的战利品喂养他。
……抑或是放弃这个计划!不去破坏,不去毁灭,只要专心地繁殖一个巢室,温暖、亲密,将人类带到那里,远离所有喧嚣与危险。世界之大,这就是它所需要的一切。
两种极端的念头,在它的大脑里来回波荡,争论不休。一会儿是前一种占据上风,令它的身体狂躁不已,快速分泌了数倍的毒液;一会儿是后一种占据上风,使它的生殖腺疼痛得像要裂开,位于口器下方的嗉囊里,同时满胀了用于筑巢的生物质,只要它张开瓣膜,就能像泄洪一样滔滔不绝地喷吐出去,淹没眼前的房间,也淹没走廊,淹没人类的每一处立足之地。
在如此矛盾,激烈的渴望中,时夜生首次体会到了惊愕与骇然交织的复杂情绪。
他只能勉力挤出一丝理智,用于思考当下的怪异情况。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我为什么会变成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