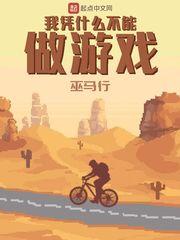笔下文学>古董局中局4 > 第一章 夜半盗墓吃现席(第1页)
第一章 夜半盗墓吃现席(第1页)
玩古董最重要的是什么?
有人说是眼光,有人说是人脉,其实都不够准确。古董这一行玩到极致,真正要讲究的就两个字:“缘分”。
所以老一辈玩古董的人,大多信命,相信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不强求。若是一件玩意儿跟你没缘分,你把它强弄到手,这叫逆天而行,会招引无穷祸患,那件古玩不再是善品,反成了噬主的凶物,轻则身败名裂,重则性命堪忧。
不过这都是老讲儿了,属于封建迷信。如今这个时代,大家接受唯物主义教育几十年,早就不信这一套。只要有钱可赚,管它什么规矩、什么路数,一概以大无畏的气魄彻底砸碎踏平。财神爷在上,牛鬼蛇神全都要靠边站。
比如此时跟我同车的那几个人,显然就不是那种敬畏传统的老派古董商人。
我现在正置身于一辆破旧的丰田九座面包车里头,车里除了司机一共只有五个人。车厢里一直特别安静,没人搭讪,也没人寒暄。那四个人端坐在自己的座位上,全都摆出一副拒人千里的淡漠表情,沉着脸一言不发。只有当车子猛然一颠的瞬间,他们才会飞快地调动眼神,假装不经意地朝彼此投去锐利的一瞥。
我能感觉到,这四个人跟我不太一样。我是城里的小古董店主,而他们则是那种专在农村收旧货的古董贩子。这些人常年混迹乡村,跟朴实却又狡黠的农民打交道,所以身上带着淡淡的土腥味和煞气。
这车里坐的都是谁?现在往哪儿去?我完全不知道。车窗关得严严实实,外头的夜色漆黑如墨,根本看不清景物。只有引擎发出低沉的嗡嗡声,表明我们正在朝着某个目标行驶。
我懒得多想,把头靠在冰凉的车窗上,太阳穴抵住窗扣,就这么似睡非睡。这车子走得晃晃悠悠,上下颠簸,我昏昏沉沉中浮起一种奇特的错觉——整个车厢就像是一具刚刚被钉起来的大棺椁,严丝合缝,不留一丝光亮。我在里头躺着,外头有十六人大杠抬着棺材一步步走过坟地,走下墓道,朝着最终的墓穴前进,前进……
对了,还没自我介绍呢。我叫许愿,已经过了而立之年,是皇城根儿下一个倒腾古董的小人物。我在琉璃厂有家小店,平时倒腾点金石玉器,店名叫作四悔斋。
哪四悔呢?是悔人、悔事、悔过、悔心。这是我爹临死前的遗言,他在“文革”期间被迫害,投了太平湖,留下这么八个字。而这八个字后头,其实还隐藏着一大段故事。我们家祖上是“明眼梅花”的一支。“明眼梅花”指的是古董行当五个古老的家族,他们各自擅长一个门类古董的鉴定,在收藏界有着泰山北斗的地位。建国以后,这五脉改组成了中华鉴古研究学会,影响力依然不小。
我爷爷许一城原来是民国时期五脉的掌门人,出身于白字门,后来因为盗卖则天明堂的玉佛头给日本人,被当成汉奸枪毙了。我们许家从此一蹶不振,退出五脉。三十岁生日那天,在有心人的推动下,我一头掉进这个旋涡里。经过一番艰苦周折,我总算是为我爷爷平反昭雪,让佛头回归祖国,了结了许家和这玉佛头的千年纠葛。事了以后,我还是回到四悔斋,继续倒腾古董,悄无声息地活着。
我突然听到一声闸瓦嘶鸣,身子猛一前倾,从回忆中醒过来。车子终于停住了,我睁开眼睛,摆了摆头。这一摆可不得了,我看到旁边车窗外的黑暗中,赫然浮现出一张惨白的人脸,脸上的双眼特别怪异,一边特别大,圆如牛眼,黑的少,白的多;一边特别小,跟王八对瞪不一定能赢。这一大一小两只眼睛,好像随时在瞄准开枪似的。
我顿时吓得一激灵,身子下意识地躲了一下,差点从座椅上掉下去。同车的四个人似笑非笑,露出鄙夷的神色。我这才想起来,这张脸应该是这辆车的司机。没容我多想,“哗啦”一声车门被拽开,司机把头探了进来,一边大眼珠子轮了轮,沙哑着嗓子做了个请的手势:“我叫大眼贼,跑堂的,几位跟着我走吧。”
我连忙调整一下呼吸,跟着其他四个人一起跳下车来。我双脚一踏上地面,一股混杂了松枝和野草的清香扑鼻而来,味道特别清凉。不用问,这是荒郊野岭的山味儿,而且是特别荒凉的地方。我环顾四周,隐隐能看见几座山形轮廓,黑暗中状如巨兽隐伏一般,似乎随时会扑过来。
大眼贼让我们跟紧他,朝着黑暗中的一个方向走去。此时天上乌云遮蔽,把月光挡得死死的,只有那大眼贼手里攥着个忽明忽暗的手电筒,勉强照亮前路。他这个手电特别有讲究,灯头罩了一圈硬纸板,这样光柱只收束在前头一段,散射不出去,稍微离远一点,就看不到了。
我们跟着他在高高低低的山坡地上走了十多分钟,七转八弯,中间还钻了两回林子。终于有人忍不住问了一句:“你这是把我们带去哪儿?到底在哪里开席?”
大眼贼转回头,咧开嘴笑道:“急什么,做东的又不会离席。”说完还嘎嘎笑了两声,声如老鸹。他笑完以后,周围温度陡然下降,森冷森冷的。那人不敢再问,只得“哼”了一声,跟着继续走。
我们一行人走了约摸半个多小时,终于走进一处幽深的山坳。这个山坳左右被两道高耸的山岭逼夹,形成一小块麓底平原。在远处隐约能听到潺潺水声,应该是从山岭上流下来的溪水,在这里盘了一圈,正好把这小山坳给切成一个三角形。溪水为底,两道山岭是两条边。这在风水上叫二龙入水,是块宜建阴宅的吉壤。
大眼贼踏进山坳,停下脚步,拿手电筒往前头晃了晃:“喏,就是那边。”我们顺着灯柱一看,首先看到的是远远一个身穿迷彩服的年轻人蹲在地上,身前有一个半米宽的土坑,坑旁搁着三个精钢柄的重铲和一大堆新鲜泥土。
不用问,这种风水宝地,土下三尺必有墓穴;有了墓穴,必然就有盗墓贼闻风而至。
“挖到什么地步了?”与我同行的一个刀疤汉子问。
大眼贼踩踩地面,得意道:“整个墓室的位置已经方出来了,咱们刚刚打到后墙。就差临门一脚,专待各位来开席。”
同行的几个人走到那盗洞前,翻弄抛出来的泥土,表情不一。我听说有积年的盗墓贼,一看土壤就知道是哪朝哪代的墓。不过我可没那本事,估计同行的几个人和我水平差不多。他们检验泥土,只为图个心安罢了,其实看不出个所以然。
检查完泥土,大眼贼笑眯眯地说道:“诸位好运气,这回上的菜是头锅的红烧肉,有吃头。要没什么异议,咱们就上菜吧?”
我们五个人点点头,站开一段距离。大眼贼拿电筒冲那边闪了一下,喊了句“开席”,那个穿迷彩服的小伙计起身,然后抓起一把铁锤和铲子。他身材细瘦,轻而易举就钻进了盗洞。大眼贼从怀里掏出一瓶散装的白酒,还有五个杯子,给我们一人递了一杯:“山里露重阴寒,整点白的驱驱寒气,还得一阵子呢。”
他不说也罢,一提这事,我顿时觉得阴风阵阵,白雾弥漫,下意识地朝黑漆漆的山林里看了一眼。大眼贼递到我这儿,笑了笑:“老弟头一回吃现席?”我尴尬地笑了笑,大眼贼道:“一回生,两回熟,咱们这个辛苦点,可心里踏实不是?”我点头连连称是,接过酒杯一饮而尽,辛辣的散装白酒顺着嗓子滚成一条火线,直到胃里,我的眼睛却一直盯着盗洞口不断抛出的泥土,心中翻腾。
这大眼贼说的“吃现席”,乃是古董界的一桩颇为隐秘的勾当,我从前只是听说,想不到如今也亲眼见识了一回。
大凡古董,主要来源有两种:一是活人世代流传下来的;二是死人带进墓里后来被挖出来的。前一种传承分明,后一种却不太好判断真假。你说这东西是从古墓里挖出来的明器,怎么证明?万一是诓人的怎么办?要知道,有些古董本身不值什么钱,价值全在它的出处。同样一粒瓜子,从小卖店买的就不值一文,若是从马王堆女尸肚子里挖出来的,就贵逾千金。
于是就有人想了个主意,先把墓地位置勘察好,盗洞打到墓室边上不动,然后请一些买家到现场来,当着他们的面敲开墓室,把坟墓里的东西掏出来,现掏现卖。买主亲眼见到明器从坟里起出来,自然不必担心有假。
这个勾当,在古董行当里就叫作“吃现席”,这个“席”原意指的不是酒席,是芦席,芦席是干吗的呢?是旧社会用来裹死人的,即指坟墓。我们这样来买东西的,叫“做客的”,盗墓的叫“跑堂的”,而“做东的”,自然就是指墓里的死人——所以刚才大眼贼一句“做东的不会离席”,吓得那些人都不吭声了。
像大眼贼说今天吃头锅的红烧肉,意思是说这是一座明墓——明太祖姓朱嘛——头锅是说之前没盗洞,里面藏着好东西的概率很高。
我们边喝白酒边等,等了十多分钟,大眼贼忽然眼睛一眯,说:“来了。”一群人目光朝盗洞看去,看到两只灰败的死人手缓缓伸出来,不是墓主诈尸顺着盗洞爬出来了吧?这场景可着实有点瘆人,大家下意识地退了一步。大眼贼却哈哈一笑,手电一晃,我们这才看清,那手是刚才下洞那小伙子的,沾满了墓泥,两手之间,还抱着一样东西。
看到这东西,大家眼睛都是一亮。看这跑堂的得用两手抱住,说明东西的尺寸小不了。在明墓里挖出这么大的物件儿,可是个好兆头。但我们五个人谁都没动,站在原地看着大眼贼一个人跑过去。
这是吃现席的规矩。买主是来买放心货的,不是来挖坟掘墓的,所以盗墓全程不能沾手,得等人家把明器送到跟前,才能看。这样一来,自己只算是买明器,不算盗墓,损不着阴德,算是个心理安慰。从现代法律角度考虑,万一真东窗事发,也最多是个销赃的罪名。
大眼贼走过去把东西接出来,很快折返回来,小心翼翼搁到地上,拿手电去晃。我们五个人凑过去一看,这东西是个瓶子,撇口,长颈,瓶腹圆滚滚的,看器形可能是玉壶春瓶。但表面脏兮兮的,看不出成色。
大眼贼早有准备,先掏出一把毛刷,把上头的泥土狠狠刷了几道,又把那半瓶散装白酒打开,取了块麋子皮,蘸着酒精细细擦拭。很快这瓶子的釉色光泽显了出来,纹饰也擦清楚了,上头有青花如意头纹、卷草纹、缠枝菊纹,看起来气度不凡。
所有人的眼睛都直了,看这些特征,搞不好是个明青花,那今晚可真是大收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