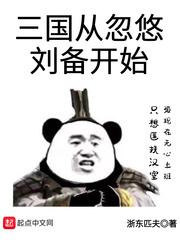笔下文学>我真的不想再努力了 > 第三百八十章 此案已无悬念(第2页)
第三百八十章 此案已无悬念(第2页)
“只怕也会终身残疾,握不得笔,吃不了饭,走不了路。”
焦作站在一旁,只觉得血液涌入了头颅,如潮汐般往来汹涌,击起巨浪滔天。揣在袖中的双手则紧紧地攥着,指甲深深地扎进了掌心,却仍然感觉不到疼痛。
有声音似从遥远之处飘来,听不清是谁的:“陛下,您看要如何处置襄侯?是任其自生自灭,还是请侍医前来诊视?”
“传侍医!”虞炟想起已经入了内库的那些黄金,一股愧疚之意油然而生:“焦令监,你亲自带人,将虞楚安置在宫里,好生给他治伤。一应伤药供给都要用最好的,从朕的内库里直接拨付,懂吗?”
“老奴明白,老奴这就去办。”焦作只觉得先前在耳边嗡嗡作响的海涛之声已经散去,整个人又恢复了清明。
公子还活着,活着就有希望。
他命小宦去取了担架,将人抬到了后宫之中的玉棠舍。虞炟年纪尚小,后宫之中空空如也,先帝留下的思太妃也挪到长乐宫去了,墨公子就算暂时住进去,也不会引起疑义。
薛温来得快极了,一见墨公子的模样便面容铁青,待全面检查过后,心中更是郁愤填积。只是当着诸多小宦的面,并不好发泄出来。
“幸好有人先行上了伤药,还接了骨。这接骨的手法极为精到,便是我也自叹弗如。”他心中知道是谁,但这会儿根本不能明说,只叹着气道:“三日。若能熬得过去,襄侯的性命才算是真正保住了。”
“那就。。。。。。麻烦薛侍医了。”焦作压着火气退了出去,一路逆着风回了承明殿。
殿中这会儿仍是灯火通明,守在门外的小宦悄声向他报告:“三位辅政大人,外加张廷尉都来了。另外,平阳大长公主也听说襄侯越狱之事,正在宫门外跪着哭呢,要陛下主持公道。。。。。。”
焦作唇角紧紧地抿着,迈步进了大殿。
虞炟高踞于御案之前,阶下上官锦正说得口沫横飞:“陛下,虞楚畏罪潜逃,此案已经没有悬念。臣请旨全城大索,同时发布通缉令,悬赏重金,死生不论,方可严肃国法,整顿纲纪。”
虞炟面无表情地望向金鑫:“金卿,方才左将军责你私纵人犯,可是真的?”
“陛下容禀。”金鑫身上铠甲未去,单膝跪地:“襄侯刑伤极重,乃是被刺客裹挟而出,并非本意。臣恐误伤了襄侯性命,是以严令不得放箭。若陛下以为臣有罪,臣,任凭陛下处置。”
“刑伤极重?”霍炫皱起了眉头:“若老夫没记错,陛下白日里曾严令不得动重刑。张廷尉,你可有什么话说?”
“臣绝不敢有违圣意。”张世昌也跪下了:“昨日审讯之时,御史中丞也在现场监刑,不过是动了几鞭而已,襄侯便已经晕厥了两回。臣不敢再问,想着待来日再审,所以方才金大人所说的刑伤极重,怕是因着襄侯体质弱于常人,是以。。。。。。”
“呵呵。”上官锦听到这里,干脆仰头笑了起来:“金大人也曾是杀伐果决的能臣,如今却被一小儿戏耍于股掌之间。那虞楚不过是畏惧刑罚特意作态,此刻人都不知道跑到哪儿去了。金大人方才的话,莫非是为了给自己脱罪,刻意而为吗?”
金鑫向来以谨慎忍隐而着称,并不擅长口舌之争。
“臣所言句句属实。”他垂首道:“臣见到襄侯之时,他已经伤重接近不治,所以才会被人劫掳而去。当时见到襄侯的人非止臣一个,南军都侯陈方,现在就候在殿外,陛下可传唤他上殿问讯。”